
大學時代的高岩
【看中國2018年4月6日訊】2017年,羅茜茜在時隔18年後挺身而出,舉報了北航教授陳小武的長期性侵行為。2018年伊始,我的北大校友王敖揭發了UIUC的徐鋼的長期性侵行為。
我由衷地欽佩羅茜茜與王敖的勇氣與正義感,特別是為弱者挺身而出的決心和毅力。
現在,作為真實歷史的見證者,我想向大家隆重推出可以和陳小武、徐鋼二位「媲美」甚至「更勝一籌」的另一位對女生性侵的慣犯——瀋陽教授。瀋陽教授,1955年生人,現年63歲,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並於近年獲得一項「長江學者」桂冠稱號。
我要說:20年前,一位名叫高岩的北大女生,正是因為遭受瀋陽教授的性侵和污蔑而死的。
我叫李悠悠,北大社會學學士,北大傳播學碩士,在美國讀過法律,目前定居於加拿大。我和高岩從高中時就是同窗好朋友。1995年,我倆一起考入北京大學,同住在一棟宿舍樓,寢室離得很近。我倆可謂知己與閨蜜,有些跟父母也不會說的話,我們都會告訴彼此。
高岩讀的是中文系。不幸的是,當時在北大中文系剛博士畢業3年的瀋陽副教授,成為了高岩他們1995中文系本科生大一的「現代漢語」課的授課老師。

瀋陽教授
那時,他40歲,高岩19歲。
瀋老師當時已婚,有孩子。至今,瀋老師還在他的60歲回憶文章裡,提及他的家庭美滿、妻賢子慧。
1995年秋天,大一剛開學不久,瀋就指定高岩當學習委員,負責文學、語言和文獻三個班一共70名左右同學的收發作業以及收錢等班務。高岩是個極其認真的女孩子,在勤奮學習之餘,她一直盡心盡力地去完成老師交給的工作,對於瀋老師的委任沒有感覺到任何異樣。
當年,大一的文科生(除外語學院外)都要在昌平園就讀一年,待大二才能返回燕園繼續學習。因我和高岩都是北京女生,每逢週六下午,我們都會回到城裡的家中,週日再趕回學校(當時是單休日,只歇一天)。開始都是我和高岩一起坐昌平的公共汽車回到城裡,再在週日下午去德勝門等學生校車回昌平園。後來,有一天,她告訴我,瀋陽老師幫他跟管老師校車的人說了,她以後可以搭老師的校車回燕園,週一早上再從燕園搭教師班車回昌平園。我當時想,這個叫瀋陽的老師真好啊,這麼體貼學生。當年19歲的我和她,根本未曾想到瀋老師這種「特殊照顧」背後的用心,更沒有想到,為什麼瀋老師不照顧其他女生也搭班車呢?
高岩家住在長安商場附近,瀋陽家住在三里河一代,步行距離10分鐘。高岩跟我說,瀋陽老師每個週一的早上會在長安商場門口的過街天橋附近等她,和她一起去燕園,然後再回昌平園。作為一個家教很好的乖乖女,天真爛漫、初涉世事的她,當初每提起瀋老師時,都是恭敬有加的。
高岩學習很勤奮,筆記記得娟秀工整,書籍讀得通通透透。當年,我們都穿著素淨的北大校服,梳著樸素的學生頭,背著書包穿梭在教學樓和宿舍樓之間,很享受地過著我們的「象牙塔」生活。在我的好朋友那飽滿的大腦門下,閃爍著一雙晶亮的大眼睛,似乎這個世界有太多好奇在等著她去探索和發現。輕聲細語的交談之際,常見她燦爛的笑容瞬間綻放,亮得如同昌平山裡的藍天,沒有一絲雜質。
大一第一學期,高岩的學習成績就在強手如雲的北大95中文系文學班裡,排在第一名。
如果一切都能停留在這樣的景象裡,那就好了。

高岩當年的專業課書籍,包上了古典的國畫書皮

高岩當年的課堂筆記,工整的藍色鋼筆字,記得一絲不苟
1996年春夏,大一的下半學期,有一次,高岩突然跟我說起:「瀋陽老師讓我把作業送到他家,還說要專門跟我討論一下我感興趣的一個語言學問題。他告訴了我他家的門牌號碼,我就按他說的時間去敲門。進門後,他說先給我倒杯水喝。我等著的功夫,看見他寫字臺的玻璃板下壓著一些家人的照片之類的東西,就面朝寫字臺微微低著頭看著……這會兒,突然,他從背後把我給抱住了。我說:‘您這是幹嘛?’他說,‘不幹嘛。’我說,「您還沒跟我討論那個學術問題呢?」他說,‘一會兒就討論。’然後,他就開始親我的臉。我聽到自己的耳朵邊響著他呼呼的喘氣聲,很害怕。」……
從這次「學術懇談」事件起,一直到大二我們回到燕園,我一天天發現,這個一向笑得無憂無慮的女孩兒,一日更比一日地變得不快樂了。
即便如此,她大一第二學期的成績依然是文學班上的第一名。
1996年秋天,我們從昌平園搬回了燕園。大二上學期的一天,高岩又吞吞吐吐地跟我說:「他(瀋陽)像餓狼一樣向我身上扑過來。」說這話的時候,她的眼睛裡盈滿了淚水。相識四年多了,我第一次在這雙純真、充滿靈氣的大眼睛裡,讀到了深深的恐懼與焦慮。
從「學術懇談」到「餓狼扑身」,不過幾個月的時間,我發現,事情越來越不對勁了。我們當時就住在31樓的同一層,我也很樂意能跟她聊天。但這時,她的話題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關於瀋陽老師的。而且,每次說到後來,都是如鯁在喉,似有難言之隱。而且,那雙晶亮的大眼睛裡,往日常見的盈盈的笑意消退了,常常是被淚水所浸潤,偶爾的微笑也都變成了苦笑。她陸陸續續跟我說起過,瀋老師脫光了她的衣服,對她做了她從未做過的事兒。她感覺到很害怕、很痛苦。她說,他侵犯了我。她跟瀋陽老師說過,她不喜歡這樣,不想再這樣了。她說,瀋陽老師說因為愛她才這樣對她,但她覺得愛不應該是這樣的。
而更讓高岩料想不到的是:瀋老師在「因為愛」對她做「她不喜歡做的事」的同時,又在和同班另外的女生頻繁約會,而且也發生了性行為。
更加無恥的是,瀋陽跟那一名女生說:「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高岩,是她主動往我身上貼的,是她勾引我上床的。你比她漂亮多了,我怎麼可能會喜歡她?是她自己精神病。」而這個女生不知出於何種動機,又把瀋陽的原話傳到了高岩同宿舍的女生以及同班其他女生的耳朵裡。
於是,一時間,謠言四起,一些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議論高岩「單戀」老師瀋陽,還附和瀋某的讕言,說她「神經病」。自此,高岩開始承受雙重的侵犯和打擊:性侵與謠言,折磨得她身心俱憊。她開始想躲開這個他、那個她和這群人,她提出想休學。後來,「休學」的事因故一時擱淺,反過來又更加重了高岩的痛苦和煎熬。
1997年夏天,大二結束後的那個暑假,瀋陽約高岩在一家飯館吃飯。這次,按高岩自己的話說,她「再也不想和瀋陽見面,只想最後和他談談」。她對他表明瞭自己對他的行為的不解與憤怒,希望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可瀋陽非但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有任何不妥,而且還對高岩冷嘲熱諷。氣得高岩一口飯都沒吃,就憤然離開了。據家人後來講,在她回到自家小區裡的時候,連鄰居叔叔都注意到了這孩子臉色很不好,好像出了什麼事兒……
1997年的秋冬,高岩渡過了她短暫的21年人生裡最悲愴與艱辛的幾個月。
1998年3月11日,高岩決絕地以自殺的方式,離開了這個她曾經格外熱愛和眷戀著的世界。

1998年3月11日,高岩離世。2018年3月11日,高岩20年忌日,高岩父母給愛女掃墓
岩去世後,很多人都參加了她的追悼會,其中包括我和其他幾位高岩的高中同學和好友,還包括我們高中的班主任劉老師,更包括95中文本科班上的不少同學和當時的班主任王宇根老師,還有其他的北大師生。而唯獨那個姓瀋的沒有出現。眾所周知,至少95中文系的70餘名同學都知道,瀋老師跟高岩的關係是最好的。對自己一直賞識的得意門生、親自指定當學習委員的好學生、主動照顧她搭班車並單獨進行「學術懇談」的重點培養的弟子,一朝倏然離世,身為「恩師」居然不見了蹤影,情何以堪,「禮」又安在?
更加不可容忍的是,瀋陽教授在高岩離世後的20年間,不時在他「神聖」的講台上,對著天真的學生們,編造著一個「神話」,那就是曾經有一個女生,大家都亂傳她是為他而死的,這根本就是個謠言,因為這個女生是個「神經病」。
可能是瀋陽教授覺得這還不夠吧。2016年,在一篇他本人的回憶文章《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風景一瞥》(刊於《甲子學者治學談》一書)裡,洋洋萬言地講述完自己成功的標桿式人生後,突兀地寫道:「1998年有一個女孩子在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後很多人認為這件事與我有關,甚至傳為桃色事件……或許當時我(其實也不僅是或不該是我),真的應該能夠做些什麼去幫助她,那這個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但願那個孩子不再受那種可怕病痛的折磨……」
在貌似「同情」的語言表象之下,瀋陽否認了高岩之死與自己有關。但如果確是如此,既然問心無愧,又為何在晒了自己幾十年的一路凱歌一路瀟灑之後,在同一文中又突然提到「我也不是沒有‘滑鐵盧’」呢?他在文中寫到,他人生中的「滑鐵盧」是語言學未被評為一級學科。但很多當年在中文系任過教或讀過書的人都清楚地記得,在高岩去世後,瀋老師曾被給予過行政處分。瀋陽也正是在高岩死後和他自己被給予處分後,突然離京,去香港某大學訪問了一段時間,然後又重返北大的。
所以,瀋教授,不是「很多人認為這件事與我有關」,而是這件事眾所周知,確確實實是與你有關的。
又據目擊、耳聞者說,在高岩剛剛去世、人們議論紛紛之際,你曾大言不慚地說:「有人為我自殺,說明我有魅力。」瀋教授,你太不要臉了!如果一個遭你性侵、不堪羞辱而自殺的女生的死亡,都能被你用來作為證明自我魅力的註腳的話,那你還在這裡兔死狐悲什麼勁兒呢?
「不僅是或不該是我」,那應該是誰呢?——請你告訴我,請你告訴高岩的在天之靈,請你告訴高岩悲傷的父母,請你告訴95級中文系的所有師生,請你告訴所有人,這個人究竟是誰?
「但願那個孩子不再受那種可怕病痛的折磨」——你還知道高岩當時還是個孩子嗎?那個年齡連你的一半還不到的孩子?那你為什麼餓狼扑食般奪走了她的貞操、青春、夢想與所有美好的信仰和希望呢?你還想對大眾散佈說高岩有病。請問證據何在?「折磨」(如你所說)她的,到底是「病痛」,還是你那殺人不見血的性侵和污蔑?
瀋陽教授回憶文章中關於高岩的部分,原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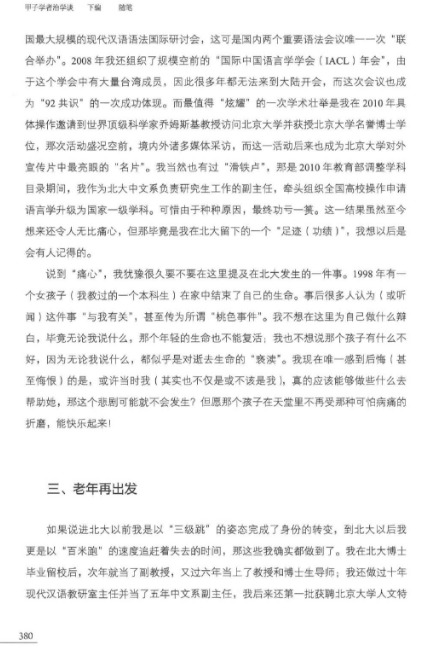
20年前,高岩之死,令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對高等學府「象牙塔」、「世外桃源」的憧憬和想像,徹底地遭到了顛覆。
20年後,瀋教授憶甲子、晒輝煌的無恥之文,又刷新了我對「恥感」的下限認知。我為母校北大有你這樣的教員感到恥辱,我為名校南大有你這樣的系主任感到悲哀。
20年過去了,你的一貫謊言連同你的一貫罪惡,該終結了。
瀋陽,請你道歉!
瀋陽,請你向含冤死去的高岩道歉!
瀋陽,請你向她年邁多病的父母道歉!
瀋陽,請你向北大95級中文系的所有同學道歉!
瀋陽,請你向所有的北大同學道歉!
瀋陽,請你向所有被你侵犯過的女生道歉!
目前,我本人對瀋陽教授尚無法律訴求。但我堅決捍衛過去和現在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保留其法律訴求、追究瀋陽罪責的神聖權利。
所謂性侵,指任何未經同意的性行為。換言之,即使對方沒有說「no」(不,絕對不行),只要她或他沒有說「yes」(是,可以),而你卻跟人家發生了性關係,就已然構成了性侵。可見,對方是否知情與許可,是界定性侵的主要標準。
(本文提及的性侵,並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師風、師德意義上的概念。)
